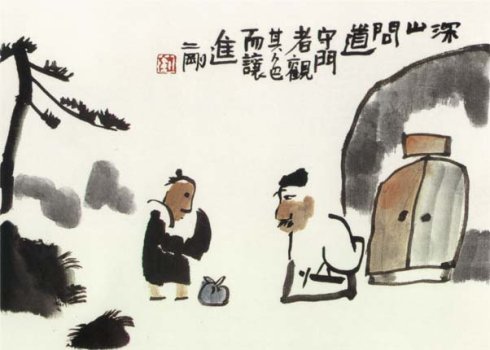

最初我留心刘二刚先生,是他的文章。他是画家,称作“新文人画代表性人物”,成就当然在画,文呢,乃画之余事。记得读过他一个文章,题目颇具戏谑,曰《画不够,文来凑》,大约说文人画上的题跋,密密麻麻的题字,把画里的空间都题满了,真的是“画不够,文来凑”。当然文外有意,弦外有音。哪知,画是妙画,文则妙文,有好事者集成一卷,放在哪些作家的文集堆里,也一点不逊色,自有另外的好处,当然喜欢读的也并不少。
此类文字,虽是画外营生,终究与画息息相关,或写些作画心得,或因画联想,弹古论今,不一而足,可谓自由。文体上多取随笔,腹笥丰盈的,罗于心中,往往因画所触媒,浮想联翩,亦庄亦谐;也有作诗词的,打得酱油,越是谐谑,或者反而更具有天真的妙趣,皆是见其性情的绝妙好辞。文章,姑且把诗词、打油种种也视作文章,当然脱略、洒然,不坐禅不礼佛,专是一样吃肉喝酒,无酸腐臭气,全秉天然。这才是天地间的第一等好文字。


惜哉惜哉,这般文字,不敢说无,实也不多,文人中,或说所谓作家,文章作手,曰舍我其谁?然睥睨者不可一世,可堪入目而观者却凤毛麟角;画家里那几个大师,古的不说,近人也只有一个白石翁,嬉笑怒骂,可见真趣。还有没有?不敢说有也不敢说无。近些年来,读二刚先生文字,仿佛有此妙者,或者竟是例外。

说来也幸运,幸而得读他这本《一个宇宙一个人》。当时吓了一跳。眼皮底浅的或说他狂,也不妨狂的,不能有傲气,却不可无傲骨。他的狂可以这么来看的,不妨当一种个性的张扬,人无个性,混在一大群人中揖让樽俎,咸尔维新,则是没大出息的。刘二刚先生不耐烦这么活一辈子,他有个性。画画上,我们一目了然,说这是刘二刚的画。文章呢,这儿一读,不是别人的,是刘二刚的文字。为人也是刘二刚的,这更不奇怪。就说吃茶吧,中国人谁不喝茶?文人更是东南西北,大家喝得风雅,那么都这么端着架子,迈个八方步的,文人的样子是装出来了;可是,刘二刚先生不干呀,累都累得死人,还活不活?他说,用一个大茶杯,抓一把茶叶,开水一泡就完事儿。此事见于他的文章《功夫茶》。他可也不是真的反对功夫茶,他也真有体会,其中甚至有很深刻的哲理:吃茶一人饮,二人饮,或者多人饮,感觉是不同的。如何一个不同?他不说,说了乏趣,这是画里的留白,让你自己琢磨,不同人有不同人的想法。
当然,我们读刘二刚的文章,也可以各有不同的读法,喜欢与不喜欢,悉听尊便。但刘二刚先生这里只管写他自己的。他的文章,其实有一个好处,即随意,不扮教师的那个讨厌脸孔,训人其实最糟糕,凭什么呢?不如玩儿。看他的写文章,我们完全可以,其实也何妨说应该,与他的画对读,有一脉相承处,或者说互相参照,读后更可领略此中之妙。文与画,在他原是不大分得清楚的,或者都一样的涂鸦,画画作文,原看兴致。兴之所指,或文或画,亦文亦画,畅快淋漓,或者此时有谁在场时,即可以见他搠毫顾盼,似乎已何假南面而王了。

最是看不惯那些假道学意味的,何妨就是一个顽童,有人怕这个形象,他却不怕的,文章怎么写畅意就怎么写。其中不少是他到过那儿,或者喜欢或者难忘,就走笔成文,那么是游记了,却也难说。其实在二刚先生笔下,什么文章的法则能够让他就范?他写他的,该怎么着就怎么着,那么,文章我们不敢轻言它的好坏,反正野趣十足,也因此生机蓬勃。比如荒地上不知名的野花,当然不名贵,但荒野里开得热闹,漫山遍野,满满当当的朝气,也就成了生动的风景。
他就这么野去,如疯长的草。绿盈盈,长条的叶儿,骨朵的小花,蓝或粉红,风来摇曳,如梦如幻;有时雨来,它也缀着晶莹的水珠儿,铃铛铃铛,仿佛可以听见它高兴的笑声。此时,我恰好在读他的《一个宇宙一个人》。